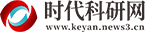领读| 小静
十点人物志原创
今天我们继续阅读刘静的作品《父母爱情》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昨天我们读到因为一张照片,“我”的父亲母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,谁也不愿让谁。
这风波会带来什么影响呢?他们的生活又会如何前进呢?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。
灾难开启
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,我父亲难得在家。那天他兴致极好,见我们正围在案板前包饺子,就挽起袖子一起干开了。
门被小哥撞开,被他同时撞开的,还有一扇看不见的灾难之门。
跟在小哥身后的人,我们没见过,但我们又分明都认识他,那张国字脸,还有我父亲家祖传的鼻子:高挺的鼻梁上方那明显的凸突。
他大约二十岁出头,穿着一身粗布衣裤,高高的个头,留着一种剃刀剃到头顶时戛然而止的头发,我们笑称“锅盖头”。
他站在我小哥身后,像个走错门的不速之客,脸上被血充得红彤彤、汗津津的。他立在那儿,一双方口的很笨很拙的布鞋拘谨地拧在一起。
我的父亲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,举着两只沾着白面的手,疑惑地问:“你找谁?”
那农村青年上下嘴唇翕动着,努力了几次也没发出音来,那双忧郁的眼睛突然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,他哽咽着,费劲地叫出了一声“爹!”
我父亲的两只眼睛马上就骇得圆住了。他惊慌失措地望了望站的站、坐的坐的我们,又望着那喊他“爹”的农村青年,嘶哑着声音又问:“你叫谁?叫谁爹?”
那清癯的国字脸上的泪珠越滚越多,他突然蹲下身,双手捂住锅盖头,又大着声哽咽了句“爹!”
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我急忙转过头去,见我母亲把手里的擀面杖往案板上一丢,站起身来,拍了拍手上的面粉,一脚踢开凳子,向她的卧室走去。
房门在她身后轰然震响,吓了我们一跳。我父亲看了看蹲在地下哭泣的农村青年,又看了看惊骇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我们,掩饰地拍了拍手,也很快地钻进了卧室。
我的姐姐和哥哥们气愤地盯住地下这个抱头而泣的人,我的小哥甚至还用回力球鞋踢了踢那双又笨又拙的黑布鞋,恶声恶气地说“你来干吗?你滚!你滚!”
我二姐大声制止了小哥,厌恶地望了望地下这黑糊糊的一团,—甩头说:“走!我们走!”率先离开了饭厅。
我记不清那天的饺子吃了还是没吃,只记得那晚那个管我父亲叫爹的农村青年,被公务员小黄领到招待所住下,我们还空着几间房的家,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。
母亲出走
第二天一大早,我母亲红着一双肿眼赶第一班客船出岛,回青岛娘家了,我甚至都不知母亲的出走。
我起床到卫生间冼漱时,小姐叼着牙刷吐着满嘴的白沫神神秘秘地告诉我:“咱妈不辞而別了!”
第二天晚上,那农村青年住进了家里,住到了大哥当兵前的房里。那间长子的住房,他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
那晚,我父亲和他关上房门,在房间里嗡嗡地谈到了好晚好晚。
我们对父亲这种背着我们谈话的举动很气愤,同时也很惊恐,生怕父亲会背着我们把原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给了他。
我们几个轮番把耳朵贴到门上的钥匙孔上,耳朵都要挤扁了,还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小哥气急败坏地朝门上踢了一脚,发出了很响的“咣”的一声。
父亲拉开门站在门口,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喝道:“谁?是谁?”我们躲在各自的房间不坑声,听着父亲愤怒地发问。
那农村小伙在我们家呆得真是可怜。那是秋天,岛上的学校有秋假。他没来以前,我们像野兔一样不到开饭号响,一般是不回家的。
自从他来了,我们几个像他会把这个家偷去似的,一刻也不离开这座红色瓦顶的房子。
我们故意在一起亲亲密密、热热闹闹地大声说笑,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乱窜,把房门摔得噼啪乱响,以示我们主人翁的权利和气派。
我们故意不搭理他,甚至不用正眼看他。吃饭时,我们又故意挑挑拣拣,大声批评小食堂的炒菜越来越不像话,显示一种对饭菜的漫不经心和满不在乎。
他一般都是缩在饭桌上的一角,拿着一个馒头或捧着一碗米饭。筷子很少用,很少往菜盘里伸。
我看得出,一个馒头或一碗米饭对他是远远不够的,但每顿他都是吃完一个馒头或一碗米饭就坚决打住,决不再拿第二个馒头或盛第二碗饭。
他很孤单。没人跟他说话也没人搭理他,甚至我父亲,也就是他爹,对他也抱有一丝怀疑,或是反感。我也说不大上,只觉得父亲看他时的眼神和神态奇怪极了。
开始的时候,公务员小黄还跟他聊聊天说说话,我小姐私下里警告了小黄,不准小黄再理他。
小黄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尽量避着他,躲着他,能不说话尽量不说,实在要说,也是嗯嗯呀呀地应付。
他不能走出这个院子,这大概是我父亲对他提出的要求。也许我父亲是怕这个跟自己长得很接近的面孔露出去,会引起不必要的轰动和麻烦。
于是,他就成天呆在这个院子和这幢房子里,和一群敌视他,处处给他难堪的人在一起,孤单、苦闷和难受是可想而知的。
母亲归来
文学启发了我的善良。我对那种恶毒的、故意的举动,实在做不下去也看不下去了,就偷偷地跟他有了往来。
我发现他每天早晨洗脸时从不在卫生间,我从房间的玻璃窗上,看他弯着腰站在院里的自来水龙头前,捧起凉水往脸上撩。
那已是深秋,岛上深秋的早晚格外的凉,早上院里甚至有了一层白白的霜露。
他大概连洗脸毛巾也没有,洗完了脸总是抬起两只胳膊,轮流地抹着脸上的水珠子。我偷偷找来一条新毛巾,偷偷地交给他。
我问他:“你有洗漱工具吗?”他听不懂的样子,直着眼珠望着我。我进一步解释“牙刷,刷牙工具”。他听明白了,就摇了摇头。
我飞跑进储藏室,找出一支新牙刷和一管新牙膏,过分热情地把牙膏挤到牙刷上,教给他刷牙的姿势和动作。
他瞬间脸红了,很难为情的样子,我因此就有了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现在想来,这实在是对他的另一种形式的折磨和摧残。
像是一条吮过水的软鞭子,唰唰地抽在他年轻结实的肢体上。这甚至比我的哥哥姐姐们更恶毒。
但我实在是出自一种善良,是经过文学启发了的善良。如果非要算是恶毒,也要算是善良的恶毒。
一个月后,他被我父亲弄到宁波东海舰队一个老战友手下当兵去了。临走前的一个晚上,他穿着我父亲的一套旧军装走进我的房间。
当时我正在台灯下赶着做秋假作业,他站在房子当中,看着被台灯拉长在石灰墙上的我的影子,不好意思地向我道别。他说:“小妹,我要走了。”
小妹!我上边有一大堆的哥哥姐姐,他们没有一个这样郑重其事地叫过我一声小妹。他们总是拖着长音,心不在焉地喊我“老七”或“小老七”。
他这一声小妹,叫得我既高兴又难过,我想回报他,叫他一声大哥,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对不起我的真大哥。
我在台灯昏暗的光线下,含含糊糊地向他点了点头,嘴里嘟囔了一声,连我自己都不知说的是什么。
母亲从青岛回来了,母亲是在姨妈的陪同下回来的。母亲像是豁然想开了一样,脸上挂着一种彻底的无所谓。
母亲对父亲的态度放得更开了,她像是一个好猎手那样捏住父亲的一条尾巴,想什么时候扯一扯就什么时候扯一扯,想什么时候拽一拽就什么时候拽一拽。
过去她还对父亲偶尔的脾气避一避,现在她可以迎面而上向父亲开顶风船了。一次,忘了为什么,父亲冲着母亲发脾气,母亲可不吃他这一套。
母亲叉着腰伸出一只依然纤细的手指头点着我父亲说:“你给我少来这套!我也只是藏了一张照片,你倒好,藏了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大儿子!你多能啊,多有本事啊!”
父亲像那右派姨夫一样,脸马上就黄了,耷拉下脑袋来一声不吭了。
结语
今天,我们读到家里突然冒出一个叫“我”父亲爹的农村小伙,给我们家带来巨大风波。
那么,这个农村小伙到底是谁呢?他真是我父亲的儿子么?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。
图片源于《父母爱情》剧照。 点【在看】,看父辈的平凡爱情点击图片,阅读更多好书点在看看父辈的平凡爱情↓↓↓